(宋明亮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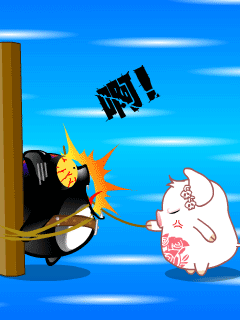
那年年前回乡下,一路飘雪。转车时又耽搁了一会,车到中堡站时,家家户户点起了灯。正当我为余下的路程焦躁时,得一就象神兵天降似的出现了。得一姓曹,排行老大,以下还有得二、得三、得四,得四的女儿是我的准外甥媳妇,我们沾着点亲。
“大舅又回来看老妈妈啦?”得一顺着他侄女叫,乡风如此。每年我都有二次回老家看母亲,一次是休假不久,一次是上船之前,雷打不动的。
“生意还好?”“村村通(公路)”后,得一买了部三机,跑短途运输,载客为主,兼代送货。两年不到,三轮换成四轮的了。
“今天不行,一个下午还没有做上一笔生意。这趟班车无论是有没有客都回去了,太冷。”说着话,得一也就顺手把我的行李归置妥了。每回如此,见着得一,基本上就没有我什么事了,得一会把我撵到副驾上等着。
车一出镇,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,西北风裹着洋面似的雪花,顺着缝隙钻进颈脖里,冷丝丝的。车前不远处,晃动着两个人影,也是一片白。“是谁,这么晚还不归窝?”得一咕哝着,随即换档、松油门,点刹,车慢了下来。灯光照、喇叭叫,两人有了反应,挪到路边,不再动,侧着身子望过来。
得一说:“是瘌广两口子,大概又是去镇上要钱了。”瘌广小时候生过头疮,成了个“毛金贵”式的人物。有人起了个头,全村老少就跟着喊他瘌广。瘌广上面有两个哥哥,就又有人演化了一下喊他三瘌广,这大概是为了对应村东的二癞嘴,还有庄西的大麻饼。乡下人口无遮栏,没什么忌讳。喊的人并无半分恶意,被喊的人更无一点气性。瘌广的婆娘妻凭夫贵被尊称为瘌三妈,客气一点的长辈也会喊她三娘(读四声)子,多半村里人反而不知道她姓什名谁。
“停一下,带一脚。”从镇上到村里五华里路,不按人头,计趟单程收币十五元。客人一上车,就是上帝。中途带客,另外收费,但必须征得先前顾客的同意并且车资酌情递减,这是潜规则。所以,我不说,得一是不会停车的,更不会自作主张。因为他知道,瘌广两口子原本就没有坐车,说明就没有坐车的打算。既然我说了带他们一起走,车钱自然是我认了。得一是认钱不论亲的,态度另说,“热情”不收费。
瘌广两口子上车后,少不了一阵寒暄。我问瘌广,“儿子还回来了?”痢广的儿子浓眉大眼,一头乌发,老子的头发都长到儿子头上了。小两口在上海郊区开一片小厂,做加工业务。
抢着回话的是三娘子:“忙,今年不回来了。”见说,我心里就有数了。“忙”是托词,躲年是真。“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”嘛。况且,留给两个老人的还有一个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,还能不想?我估摸着:想必是生意不景气。
需要做一点背景交代的是,在我们村里,有个叫“会”的民间组织。既不是官派的,也不是民选的,是村里五、七个闲汉自发的。这些闲汉并不是村痞庄霸,是一些享清闲的男子汉,都是些热心公益又有些威望的人。自打村小学撤并后,每逢年三十,敲锣打鼓给军、烈属送春联,义务的。以往是一帮村干部领着一队小学生,“会”接手后,干部们也就撤手不问了。有人说,这里面没油水,也有人说,干部们是忙更大的事了。至于更大的是什么事,只有鬼知道。年三十只是开场锣鼓,“会”里的重头戏是正月初一,全年的财政收入多半来源于这天的拜年钱。年初一拜年的程序和年三十慰问军、烈属的程序大同小异,一成不变的是,前导是一人捧着毛主席石膏像引路,紧随其后的是一人高擎着五星红旗,红旗必定是簇新簇新的,一次没有使用过。接着是两人抬着木雕关公,关公的大刀片是新打上的银粉漆,雪亮雪亮的。再往后略有不同:给军、烈属送春联是敲锣打鼓,主家会给各人发支烟。而初一拜年的对象是在经商办厂的人家,不光是敲锣打鼓,还有两人的舞龙表演。主家不光敬烟,还放炮仗,送红包。明里,红包是随主家意愿,万儿八千不嫌多,三百、五百不嫌少。当场用大字写在一张红纸上,透明得很,也就有了竞价的意味,不过这里拍卖的不是有形的物什,是生意人无形的面子。因此,区区一百块是再也拿不出手的,怕人笑话。拜年的路线是事先深思熟虑了的。头彩往往是有相当经济实力并且出手阔绰的主,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如果有两家争头彩,要经过暗箱操作,私下协商,原则上是价高者得但前提是不伤害另一方的面子。
我曾经问过“会”里的一个管事,毛主席是引路人这一点无可厚非,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也说得过去,给军、烈属送春联抬着个关公像更算贴题,关老爷是战神嘛。可是给商人拜年也抬个关公,是不是有些不伦不类,商人讲的是利,关公讲的是义,风马牛不相及,应当抬座财神才是,做生意是求财的吆。管事说,“财神不管用了,这年头还是要看谁的刀子亮。村里建了两座庙,修了一座水上戏台,又扩宽了停车场。正月十五还有个灯会,四方八村都有人来看的。所有这些开销,都有赖于关老爷的刀子快。再说,‘会’里动做生意人的刀子,对他们来说九牛一毛,人家也乐意被宰。生意场上,他们再去宰人,哪个不用刀子啊?哪个刀子动起来不狠?”
早几年,瘌广儿子的生意还行,又是个好面子的人,每年的红包都不薄。据说今年剑走偏锋,决策失误,不光亏了老本,还久下不少新债。不回来过年大概与初一拜年的事沾边,躲呗。其实,“会”并不赶尽杀绝,对困境中的生意人家还是网开一面,年照拜,红包就免了。一般地说,主家丢不起那个人,干脆找个由头南箕北斗互不照面。我度量着,瘌广儿子就是这么个情形。
得一是个聪明人,见我哪壶不开提哪壶问起他儿子来,就故意岔开话题,主动问起这几天讨债的事。抢着回答的还是三娘子,我也从三娘子的絮叨中了解到事情的梗概:
瘌广有一方紧挨着镇已停产农药厂的六亩八分水面,养殖螃蟹。七月份一场暴雨,下塌了农药厂仓库,仓库里废农药流进了瘌广的蟹塘,损失惨重。官司打到市法院,庭外和解由镇政府赔偿三千八百元。镇里说,钱是一定会赔的,但要缓一缓。这一缓,就缓过了夏天,缓过了秋天,又缓到了冬天。眼看着就到了年根,总不能拖到开春吧!瘌广夫妇一合计,就紧锣密鼓地讨起债来。
起先是找的书记,书记说“还钱的事牵涉到好几家,不是一件小事儿,得和镇长通通气。这样吧,我这里不打坝。你们去找找镇长,看看镇长怎么说。”是啊,现在都讲集体领导,不搞一言堂,书记说的在理。于是去找镇长,可是楼上楼下找了个遍,就是找不到镇长,只好打道回府。
第二天接着去,终于找着了镇长,镇长说,“还钱的事牵涉到好几家,不是一件小事儿,得和书记见个面,要书记同意才行。”三娘子赶紧说“书记昨天我们见过了,他没意见,就请您镇长高抬贵手了。”镇长说“光听你的可不行,我要见到他的人,盘子还要书记定。”“这样吧,你们去书记办公室看一看,如果在,过来说一声。”于是去找书记,楼上楼下找了个遍,就是找不到书记,有人说开会去了,有人说下乡去了,只好回家。
第三天继续去,终于见到了书记和镇长。书记和镇长说,“还钱的事牵涉到好几家,不是一件小事儿,得让财政所长想办法,看看这笔帐怎么走。这样吧,你们去一趟财政所,请所长过来一下。”于是去找所长,楼上楼下找了个遍,就是找不到所长。后来又去过几次,有时只见到书记,或者只见到镇长,就是见不到所长。
“大哥,你说说,这不明明就是赖着不给嘛?”在村人眼里,人五狗六地的我也算是个有身份的人。可是,我确确实实又不是什么这个长、那个长,但又不好直呼其名,“尊”者讳呀,村里人讲究的是不能失了礼数。于是,年长于我的、辈份高于我的,男的会招呼一声“老大”,女的往往是喊“大哥”。
我对三娘子说:“不过,你还真是拿他没办法。大面上他不是不给钱,是找不到人而巳。”
“就是这话呀,大哥,你是见大世面的,主意多,你说说,怎么弄呢?急死人了。”三娘子眼晴鼓鼓的,饱含泪花。
我说:“不要急,急也急不来。要不去找找书记或是镇长的家属,诉诉苦。女人心软,好说话。”
“大哥哎,你还当是你在家时的样啊,现在还有哪个书记镇长家在农村的?至少也是住在兴化城里,就算是真的摸到门上去,还能空着手?礼轻了人家看不上,送重了又不值当,门难进哪!”
“当初不是法院调解的吗?再找法院去。”
“不要提法院,要不是法院鬼糊弄,也不至于就赔这点点,连本钱都不够。”
“每到年底,那个城市都会发生几起讨债民工上高楼、爬电线杆子的案子,寻死觅活的。引起媒体关注了,也就有了解决的希望。”我这么说,倒不是鼓动三娘子走极端,其用意在于告诉她现在到处是债难讨。
“电视上我也看过,也学不来。”这倒是大实话,三娘子既老且矮又胖,登高作业确实有相当的难度。“再说了,上那么高,大风一吹,冻出病来还不是自己掏钱挂水。” 三娘子风险意识挺强的。去医院看病,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挂水,成了规律,也难怪我的乡亲们不说看病说挂水。
“赖的怕横的,横的怕不要命的,不要命的怕泼的。”我说:“干脆,三娘子你就撒一回泼,眼泪鼻涕一甩一把,搅得书记镇长不安生,只要瘌广不出面,还能把你妇道人家怎么样。” 这话明显就有挑唆的意思了,人们往往会将感情的天平偏向于弱势的一方,何况在三娘子这边是占理的。帮她,是站在了正义的一方。这么一想,似乎感到自己还是挺高大的。
三娘子一听,忙说:“要我当泼妇,丑死了,还不如不要这个钱了呢!”
“放屁!”一直沉默不语的瘌广突然吼了一句。“买年货要不要钱?出人情份子要不要钱?斌斌(小孙子)开学要不要钱?要你当一回泼妇就要你命了?”我也劝她说:“这泼妇是临时的,钱要回来了就不当了。又不是偷、又不是抢,要的是自己的钱,就不丑,丑的是赖帐的。”
“这泼妇也不是说当就当的,也得会呀?” 瘌广一发火,三娘子还是有所顾忌的,语气上也就跌了软。
“你不是见过得一婆娘那一次撒泼吗?”
“那我也不能抓书记镇长裤档吧?”
“谁要你抓裤档,是要你学那个泼辣样。”得一开上车后,手上也有了几个闲钱。推个牌九、打场小麻将倒也没什么,关键是有一阵子杨二寡妇动不动就请他帮忙拿趟东西、回个娘家什么的,次数多了,就有了些风言碎语。一次顶顶杠杠,得一婆娘上去一把抓住了得一裤档,得一眼泪水立马就给捏出来了。得一赌咒发誓说小寡妇每次用车都是给钱的,赌咒发誓说他们是清白的,赌咒发誓说再也不给她用车了。从此,得一婆娘一抓成名。得一也不以为耻、不以为荣,别人提起,他也津津乐道,就象是局外人。
说来凑巧,三娘子再次讨债时正好赶上上级领导要下来检查维稳工作。书记、镇长一班领导都候在镇政府大门口等大领导的车,三娘子不明就里,冲上去一手抓住书记,一手抓住镇长,狂喊乱叫:“赖皮书记,赖皮镇长,今天再拿不到钱,姑奶奶我就不走了!”
书记挠挠头,看看表,坚持不到两分钟,掏出手机打电话给财政所长:“赶紧送三千八百块钱来,把蟹塘赔款结了,要快!”
三娘子如愿拿到了钱,还逢人便说:“书记真是个大好人啊,一点都没为难我,一个电话所长就立马把钱送来了。”就当是前面几个月的种种不愉快从未没有发生过似的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