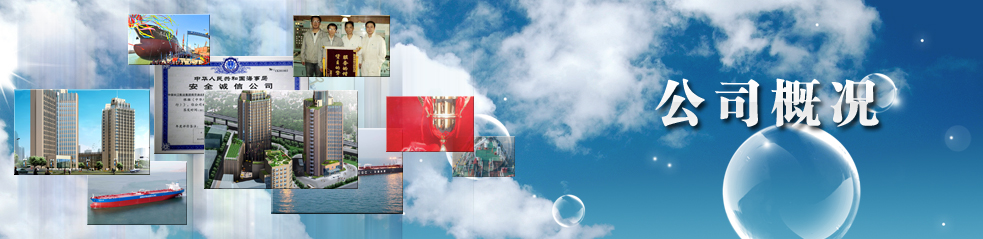(于峰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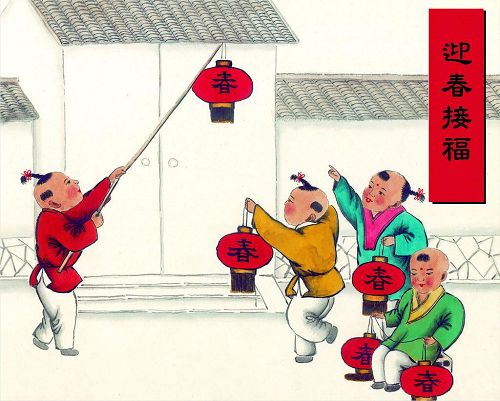
日出日落三百六,周而复始从头来。草木枯荣分四时,一岁月有十二圆。在中华九州大地之上,每年的第十二个月圆夜都是万家灯火,亮如白昼。因为这夜不同于平常,它只属于华夏子孙,称之为“除夕夜”。
翻翻日历,今天已是腊月十六,再有十四天就是“除夕夜”了,不知不觉间,又要过春节了。提到春节,中国人都会有种莫名的喜悦与冲动,这种莫名的情愫由来已久,如果一定要追溯,我想应该是4000年。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一天,舜即天子之位,带领部下人员,祭拜天地,从此人们把这天当为岁首,这就是农历新年,后来人们叫它“春节”。唐太宗李世民也写过“岁首诗”:寒辞去冬雪,暖带入春风。可见“春节”的历史已非迢迢银河可丈量。
自我记事以来,几乎每年我都会随着母亲去沂蒙山东河村外公家过春节。那里是地地道道的农历新春,庄稼人的年。
刚进入腊月,姥爷姥娘(就是外公外婆)就开始忙着备年货了:五谷杂粮,瓜果点心,鸡鸭鱼肉,彩纸炮仗……陆陆续续,一直到腊月二十九,姥爷都还要倒腾倒腾,再进点年货。那时候由于我要上学,母亲要上班,所以我们要等腊月二十八才能大包小包的赶长途车到家。到了家也顾不上疲惫,就忙着帮姥娘割肉熬汤下花生——做肉汤,然后放在院里冻上个两天两夜,最后形成肉冻,俗称“冷油”,是我们老家过年不可少的冷盘菜。第二天一大早,我就会陪着姥爷去祖坟磕头上香,然后去老屋(母亲十几岁时的住处)祭扫一下,下午就陪着母亲盘点年货,如果少了什么,姥爷就会赶着牛车带我去门市部(城里人叫超市)购置。
等到腊月三十的早上,我就和姥爷一起剪彩纸,贴春联,糊年画。每间睡房里都要贴上“抬头见喜”,堂屋中墙要挂上一个大大的福字,并且是倒过来的,那时候还小,不懂为什么要把字反过来“写”,后来才知道,那叫“福到”,院子里要贴上“满院生金”,门子的对面是“出门见喜”,树上吊着“根深叶茂”,只要是能看得见的地方绝不会落下一处,有门处要贴上正规的联子:“五谷丰登,六畜兴旺”“四方来喜,八方进宝”“米面如山厚,油盐似海深”……这些联子都是人用毛笔写的,绝无半点机械“斧凿”的痕迹,字里行间透着庄稼人的平淡朴实。贴完对联,我就喜欢蹲在灶房门口,等着里面的“厨娘”叫我:“外面的小家伙进来,尝尝咸淡。”我一听,乐得屁颠屁颠的冲进去。一天就这么忙忙碌碌,欢天喜地的过去了。晚上,不用我说,大家也知道要做些什么了:“团圆饭,守岁夜”。
守岁的习俗最早记载于西晋周处的《风土忌》:除夕之夜,各相与赠送,称为“馈岁”,酒食相邀,称为“别岁”,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,称为“守岁”。而此习俗兴起于南北朝,人们点起蜡烛或者油灯,通宵守夜,意在把一切邪魔病疫照跑驱走,期待新的一年吉祥如意。在我们那里,守岁有两层含义:年长者叫做“辞旧岁”,珍爱光阴;年幼者守岁是为延长父母的寿命。守岁还意味着辞旧迎新,所谓:一夜连双岁,五更分二年。
正月初一,你还没来得及睁开眼,耳边就开始“噼噼啪啪”的响,村前村后,全是炮仗,碎红满地,灿若云锦——好个满堂红,家家户户都要迎个新年的头彩。早上要吃汤圆,寓意团团圆圆,还要吃饺子,饺子的做法是先和面,“和”同“合”谐音,而饺子的“饺”与“交”谐音,合与交有相聚之意,所以吃饺子是合家团圆的意思。饺子里还包着“小钢镚”(硬币),谁要是吃到了,这一年就会财运滚滚、挣大钱。如果掉在锅里了,那就是有财大家一起发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为了吃到那个圆圆的硬硬的家伙,吃了三碗饺子,才吃到一个,小肚子撑得圆滚滚的,真不知道当时哪来那么大的胃,要是搁现在,说什么也吃不下两碗。后来母亲告诉我:要不是姥爷偷偷放了一个“破饺子”,你还不知道要吃几碗哩。我听了,不觉心头一动,老人对孩子的关心总是在点点滴滴的生活里。吃完饺子,母亲就领着我串门子磕头去了,姥爷姥娘是不能走得,要在家等别人来给他们磕头,这头不是白磕的,要给钱的。
正月初一一般都是儿子这边拜年。等到了初二,就是女儿们回来了,嫁出去的姑娘们在这一天,携着丈夫,孩子,带上薄饼或者饼干回娘家过年,由母亲将薄饼,饼干分给邻里,也许每家只有一小块,但情意却甚浓,表达着姑娘们对邻里乡亲的思念,真正是“礼轻情意重”。
到了正月初三,就要把初一,初二的垃圾倒掉。因为初一,初二是不可以倒垃圾的,否则就会破财。而且,初三的早上,要吃完馄饨才可以倒垃圾,因为馄饨叫做“元宝汤”,喝完馄饨汤,财宝滚进来。
初三倒完垃圾,初四晚上就得守夜到天明,大家聚在一起吃吃喝喝,到了午夜十二点,就要去路头放炮仗,接财神。点炮最好的时间就是初五零时零分,那时响起炮声就等于接了五路财神。在我们老家初五这一天还叫做“送穷日”,要吃得特别饱,叫做“填穷坑”。意思就是送走穷鬼,来年发财。
到了初七,就是村里孩子们的主宰日了。传说女娲创世,先造了鸡鸭猪狗等动物,于第七日创造了人类,所以初七叫做人日,也称“人胜节”、“人七日”。这个节俗据说始于汉朝,魏晋开始重视,始有戴“人胜”的习俗,“人胜”就是一种头饰,也叫彩胜。买不起头饰的人就剪彩为花,剪彩为人贴在窗户上。初七在老家是个重要的日子,不是因为人日,而是因为这一天要送火神。村里的孩子们要选一根木棒,在木棒上绑上两根麦桔,这就是“火神”,然后,在家门口点燃“火神”的一端,孩子们抱着“火神”往村外方向跑,直至“火神”燃尽,用以将“火神”送出家门,一年里没有火灾,平平安安。
我们家送“火神”的任务当然由我承担了,但我实在不想送“火神”,因为我送走了“火神”,姥爷姥娘就要送我走了。我要上学,母亲要上班,所以初九或者初十就是“离家日”了。
回到家,“年”就基本上过完了。就还剩一个元宵节了。过完乡村的年,再过一过小城的节,真是天壤之别。每年的元宵节,公园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,公园的广场上挂着各种各样的灯笼,有兔灯,鼠灯,花灯,船灯……五颜六色,五花八门。令人目不暇接。公园湖中心的亭子里不时的传出阵阵呐喊声,不用说一定是有人猜谜得中,拿奖了。在我的家里有一张我六岁的照片,背景就是元宵节灯会时的孔雀灯——孔雀开屏。真是不得了,那个时候不要说拍照片,那么大的灯会能让我站在台中央,真是三生有幸。听母亲说:我小时候长得胖乎乎的,白白净净,眼睛也很大,非常可爱,所以人照相的师傅一眼就相中我,让我给他做背景。听得我心里直犯嘀咕:都怪我小时候太帅气,所以现在变得“貌何以堪”啊,真是天妒英才!
这就是我记忆中的“过年”。今岁的“年”我不能再陪母亲回老家,不能再陪姥爷贴春联,因为我漂泊在大洋之上,要和“翡翠”度年。这个年究竟要怎么过,着实让我期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