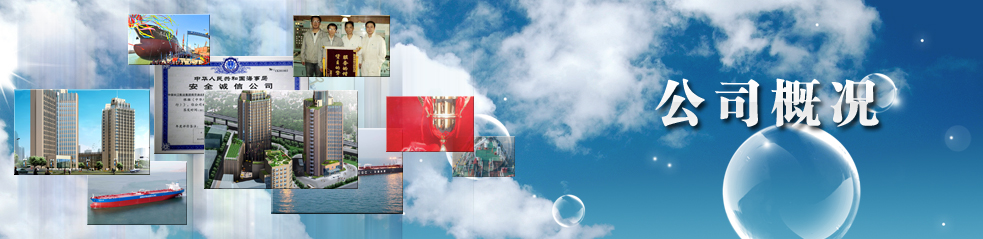岛国周游记
(刘家余)
在整个10月、11月期间,长航成功轮一直航行于太平洋岛国区域,先后经过了所罗门、斐济、西萨摩亚、美属萨摩亚、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岛这五个岛国。在这个航次即将结束的时候,回头想想,这次岛国之行还真是丰富多彩。在此我将这次的部分见闻摘录下来,以供后来的兄弟船舶们参考。
先是所罗门Solomon。如同所有的岛国一样,每个小国家都是由数个到数十个不等的小岛组成的,而其中最大最繁华的岛屿也就是首都所在地,所罗门也是一样的。我们靠泊的就是她的首都——霍尼亚拉Honiara。
霍尼亚拉没有供大型油轮靠泊的码头,这里采用的是船头抛双锚,船尾出缆绳分别系在左后方和右后方的两个浮筒上的方式。岸方有一个小小的铁皮快艇作为带缆艇。那小艇之简陋,在波浪间上下飘摇的身影,让我们看着它带缆绳都为之捏一把冷汗。岸方与船舶联系靠的也是这种小快艇。船舶系泊的地方距陆地只有300米前后,我们的对讲机完全可以带到岸上以供与船舶联系使用。船尾所对的方向就是霍尼亚拉最大的一个果蔬市场。这里有大量的水产品和水果供应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这里的石斑鱼价格只有40元一公斤前后,价格较国内极为便宜,走过路过的弟兄们千万不要错过,解馋过瘾的机会就在这里了。除了石斑鱼以外还有红鱼(一种满身鲜红色的鱼)、蓝鱼(一种足有一米多长全身深蓝色的大鱼)、龙虾等等。不过要注意了,这里的有的鱼是按照千克算的,而其他的水果、虾、蟹等几乎都是按堆或是个数的方式出售的。这里的华人很多的,到了中午和傍晚买菜的高峰时段,你可以在菜场里见到很多华人在这里选购。华人大都很热情,一旦有价格或者沟通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求助帮忙的。
然后是斐济Fiji。斐济我们经靠了苏瓦Suva和乌达Vuda两个港。苏瓦Suva是直接靠的码头。码头距外面极近,走路两分钟就可以出到外面。在码头门口有一个东北夫妇开的一家小小的集话吧、网吧、杂货店于一体的商店。在这里你可以花2-3美元与家里通话、视频,价格很是划算。还可以吃到洽洽瓜子、果粒橙等很久没有品尝过的国内零食。老板夫妇极为热情,一口地道的东北腔绝对让你感觉到家乡人的亲切。你可以先向他们询问当地的蔬菜、水果、水产品的价格再到只有一街之隔的市场上去买些补给。当然了,换钱在这里也是可以的,但是要用美元来换。与这一街之隔的市场里有大量的水果蔬菜供应,而且价格适中,较新加坡的伙食供应便宜,大家可以在这里多补充一点。顺着街往前走一点点有一个水产品街,但是价格貌似比霍尼亚拉贵一些,而且不太好讲价钱。在这边出行建议多在白天,且要两人以上出行,因为据那位东北大哥介绍当地治安较差,就连他的店前些日子都被持刀蒙面的匪人抢过,夜间也有来自国内的船员被抢的事情发生过。
乌达港Vuda是系的浮筒。据码头人员介绍上岸的话要先做小船,在到岸上叫出租车,再然后经过十几分钟的车程才能够到达小镇。因为时间有限,不建议上去,当然最主要原因还是在苏瓦港已经买了大量的水果蔬菜,这边就没有必要再跑那么远的路了。
再是西萨摩亚。我们靠泊的港口是阿皮亚Apia。因为我们靠泊的时候是周末,所以虽然我们千辛万苦找到了商场、市场和超市,但是都关着门。倒是这一路上路过的5、6个教堂里面人潮汹涌。有愿意见识下宗教方面东西的话倒可以参观一下。西萨摩亚也是一个小国家,顺着海边的长堤漫步,不一会儿你就会来到当地的总统府,早晨的话还可以看到穿着筒裙的大兵集合巡逻,很是别有一番风味。当地也有鱼市,但是好像只开到早上8点之前。但是傍晚5点钟左右的时候,长堤边上就会出现慢跑、散步和买东西的人。这边我们只遇到了两个来自国内援助的医疗队的医生。关于鱼市的消息也是从他们口中打听到的。下次如果你去那边的话可以试一下,傍晚前后在长堤边等一下,估计还可以遇到散步的他们。
再再是美属萨摩亚。这个叫做帕果帕果Pago pago的港口与西萨摩亚只有不到一百海里的地方就属于美国了。在这边靠码头要注意了,会遇到美国的USCG检查。但是检察官人很不错,讲理得很,只要前期工作到位了,态度好一点一般没有问题。出了码头大门,往左一直走可以分别遇到中国人开的超市、街边的果蔬市场、麦当劳;往右一直走可以遇到一座满是穿着绿色筒裙学生的学校、一座大型带冲凉的公厕、一片可以戏水的沙滩、一座小型的中国城。本来麦当劳应该可以上网的,但是我们的笔记本大都连接不到网络,但是沙滩边上一座宾馆有无线网络,在沙滩的凉亭下就可以用自己的手机或者电脑联接到了,所说速度慢了些,但是有的用总是好的。下午和傍晚,沙滩边的海里都是当地穿着短袖衬衫和大裤衩的人,在海里乱扑腾,整个一片欢声笑语的海洋,很是让人有加入的欲望。那个小型的中国城我也是听一个当地的小孩子说的,貌似很远要走半个钟以上的样子,我们没有去到那边,下次哪位弟兄走到那里了介绍一下哈。
最后是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岛。我们靠泊的是努美阿Noumea。也是系的浮筒。要注意的是这边说的貌似主要是法语,英语到这里貌似就没那么好用了,至少引水站的英语听了让人想发狂,码头上来的值班人员只会一点点英语,稍微复杂一点的事情就要找码头长交流了。还好引水员的英语还是很靠谱的。虽然这边离岸很近,城市也是抬眼就看得到,而且车水马龙、楼宇众多。但是没得上,所以没的介绍了。在夜间进出航道口的时候要注意下了,有一对左右红绿灯,光线极为微弱,航行的时候要瞪大眼睛了。
关于接换喉管,几乎不是8寸就是10寸,各个港都不尽相同,左右两边倒。大家就多辛苦了。还有这边天气极为炎热,室外工作绿豆汤一定不能少。太阳只要2、3个小时就可以把皮肤稍敏感一点的人暴晒掉一层皮,建议包块布在脸上,毕竟咱们还是要回家见人的!
以上就是岛国航行这近两个月来的一点点小经验,希望可以帮到大家。
岛国航行两月余,脸皮晒掉五六把。
椰树火山伴我行,碧空鲸豚啄浪花。
石斑龙虾真好大,香蕉木瓜满树挂。
若问我从哪里来,长航油运是我家。
再见,美丽的白贝壳
(郜东恩)
一位作家说过,一个好的城市一定要把自己打点出三个层次,一是打点生活,一是打点历史,一是打点自然。
在悉尼的老街上,许多陈旧的建筑朴素得像个头戴蓝布巾的村姑,安静地伫立在美艳与绰约之中,没有左顾右盼的慌张,也没有扭扭捏捏的不自在,这份从容淡定与生俱来。
城市从很大程度上来讲,是一个让人生活的地方,这些旧建筑由于设施舒适而方便,让人觉着格外的亲近。走在宽敞的人行道上,我忽然怀念起八十年代初的南京,那时那儿有一样宽敞的人行道,一样通透的天空,一样干净的阳光,还有这儿不曾有过的淅飒作响的梧桐树叶。
有些人你第一眼便觉得熟稔,有些地方你第一次面对便没有理由地喜欢。对海员来说,悉尼是值得在记忆里打扫一处干净地方存放起来的城市。在码头门口等候海员俱乐部的免费班车时,由于已到规定的时间,我们忍不住地来回张望,这时一位门卫一路小跑地来到我们身边,说这儿就是班车的等待点,车很快就会来的。又过去了五、六分钟,这位令人尊敬的门卫再次来到我们面前,告诉我们他已与班车司机联系过了,车子十分钟后到达,让我们不要着急。说实话,这样的礼遇着实让看惯冷脸的海员们有些受宠若惊。
也许友善只是善良人们生活中的一些习惯。在去悉尼市区的路上,班车司机在一个路口主动停下车,对路边犹犹豫豫的路人招了招手,示意让她先过去。这一幕我曾在报纸上见过两回,一次是说苏州,一次是在说我的家乡扬州。如果说生活是一首叙事曲的话,这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美好善意就是曲子里最温暖的音色,也正是这些一个个小音节,弹奏出了一个城市的背景音乐。
不知道悉尼有过什么样的历史,有什么值得一再提及的人和事,但悉尼可能没有在这上面下过什么功夫,或是也确实没有什么功夫可下,否则不会只要提起这个城市,人们的脑海里只会浮现出两样东西——悉尼大桥和贝壳一样的悉尼歌剧院。
在城市里打点自然是件奢侈的事,如果上天眷顾,赐你好山好水,如屯溪,如威尼斯,那另当别论。大部分城市想在闹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原生态,无疑是在为难自己。而悉尼在这方面一定是个高手,可以把这两个庞然大物打造成身体上最为灵动炫目的部分,就如美人一双明艳的眸子,看过之后便再也无法忘怀。
沿着环海大道,我们从悉尼大桥徒步来到神往已久的悉尼歌剧院。没有想象中的洁白,也没有想象中的高大,但当你置身在飞扬的贝壳之下时,你的心灵也随之轻快起来。一路上,摆放在美丽鲜花间的葡萄美酒,吹奏着忧伤萨克斯的流浪艺人,慵懒踱步于欢乐人群中的红嘴海鸥,都成为这场美景最具情韵的点缀。
海风沁人心脾,景色美轮美奂,不同肤色的游人们流连于巨大白色贝壳四周,以各自的方式记录着属于自己的兴奋,而这白贝壳却独行特立,静静地注视着自己面前的一片静海。
临别时分,悉尼怕自己还美得不够,收敛起明媚阳光,淅淅沥沥地飘起几滴小雨,为动人的脸庞又添上几分水色。
再见,悉尼!再见,美丽的白贝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