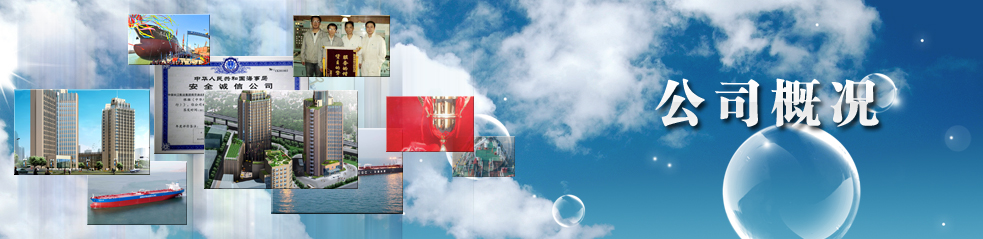(陈满林)
前几天在阿曼卸油,电视可以收看当地的电视节目。虽然听不懂,但看看画面也不错,特别是体育节目,不听解说完全可以欣赏。偶然看到一档介绍中医的节目,倍感亲切,每天准点收看,画面上的钢针、火罐、中药,药铺药柜上写的枸杞、陈皮等汉字,经典里繁体竖书的中文无一不让人自豪。可是在第三天,当画面出现一些韩文及桌上的韩英大字典时,我疑惑了,想到序幕中不断出现的东医字样,我明白了——可能是韩国人在宣传中医。只是他们不是在帮我们宣传,而是在为他们自己宣传。这样在阿曼人的眼中,中医便是韩国人的国粹了。当时的感觉就像在品美味时发现死苍蝇一样恶心,愤怒不亚于看到兽首在法国拍卖,想说的就两个字强盗。
从申遗端午祭,到抢夺孔子,韩国人处处走在我们前面,现在在中医的宣传上又走再我们前面了,这样文化抢夺比盗窃实物更甚,当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。
韩剧《大长吟》在国内热播后,我女儿居然问我针灸是不是从韩国传到中国来的。可悲吧!传统文化因为宣传不力出现如此尴尬的局面,能光指责韩国人吗?
检讨一下发现,武术没有走向世界,国内却到处是跆拳道、柔道馆;中医没有发扬光大,中医院成为难以为济的鸡肋;传统戏剧后继乏人;传统书籍无人问津;传统养生术成为赚钱工具。绿豆治百病,泥鳅成神方。少林寺成为上市公司,方丈成为董事长,少林武术也伦为舞术。如此对待传统文化,怎么能在国际上宣传我们的传统文化呢。
“洋为中用,古为今用”这二条腿本来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。可现在变成金鸡独立了,英语从幼教开始到大学不掇,而且有专门的四六级考试,不过关者不予毕业。而文言文初中开始上,高中主学,大学选修,没有专门的等级考试,国人通读过《论语》、《道德经》者罕见,更不谈《墨子》、《韩非子》了。传统典籍如何让人学?
我们不学,外国人在研究,这就是为何外国学者到中国来与我们谈话时会觉得无所适从,因为他们学的中文都是优秀的传统文化,而我们却没有深入研究。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何谓“道可道非常道”?我们大多数人只会摇头。一问三不知的结果会不会让他们感慨中国人学中文吗?其实还真有人提出高考不考语文,以后我们中国人可能真的不学中文了。中文都不学了,还用得着学习传统文化吗?
刺激我的远不止这些,在《读者》上看到一则外国人写的故事,说一个国王看大好河山竟哭了起来,说我的国家如此的美好,我却不能一直拥有,真是可悲啊。众臣跟着迎合说:“我们跟着享受美好的生活,都舍不得死,何况国王您呢。大自然真是太不公平了,怎么不让我们伟大的国王长生不老呢。”于时一起号啕大哭起来。只有一个大臣在旁边冷笑。国王很生气,问他笑什么。他说我笑一个愚昧的国君和一群阿谀奉承的臣子。如果人不死的话,比您强的祖辈会把皇位交给您吗,我怕您现在还在地里种田呢,那有心事来考虑长生不老的问题呢。而这些臣子见皇上犯错不劝谏反而在这里奉承着陪你哭,您不觉得好笑吗?为此作者也发了一些感慨。显然《读者》杂志是觉得这个故事能给人以启迪才介绍给我们的,可他们恐怕不知道这个故事其实发生在我国的春秋时代的齐国。讲的就是齐景公与名臣晏子故事,所以《读者》杂志未作注解。读过这篇文章后,我比齐景公还要伤心。我们不了解自己历史文化竟到了这种程度,我们靠别人来津津有味地读自己的故事,靠别人来启迪我们的人生。
文化是国家的灵魂,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。我们应该砸碎封建礼教的形式即仪而保留其礼的精神即敬,时代需要乐的和谐,也需要礼的敬畏。
我们的先辈不乏杀身成仁,舍生取义之人。赵襄子的侍卫官、豫让的朋友,在发现豫让有刺杀赵襄子的图谋之后,为不背朋友之义,不违君臣之道而自杀;楚国的刑侦队长石遂在追捕杀人犯时,发现犯人竟是自己的父亲,毅然地放走了自己父亲以显其孝,但他尊重法律,在国君面前以渎职罪砍下了自己的头,维护了法律的尊严。他们的行为让我震撼!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乏思想的灵光、智慧的火花。《诗经》教人温柔敦厚;《尚书》教人疏通知远.《乐经》教人广博易良.《易经》教人絜静精微.《礼记》教人恭俭庄敬.《春秋》教人属辞比事。
民族在振兴,国家正富强,社会已进步,传统文化必需发扬光大,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是中华文化的四海远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