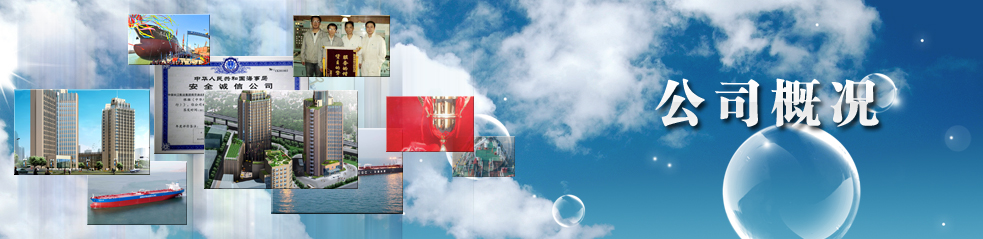——写在《长江航运报》创刊六十周年之际
前段时间的一个早上,我接到一个电话,是退休在家的老政委牟成炳打来的。在通报姓名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:伙计,混不错啊,在海外旅游。我说:没有啊,我可从来没有出去旅游过,休假都窝在家里,更不要说海外旅游了。他说:因为感冒我昨天到长航职工医院看病,在《长江航运报》上看到你的文章了,《斐济印象》是你的旅游经历吧。我说:哦,原来如此啊。他说:你们现在真好,周游列国,免费旅游。哪像以前我们就在长江一线跑,不是武汉就是九江、安庆。我说:沾公司发展的光,现在我们公司的船遍布世界各地,在外国经常看到长航集团旗下的船,现在的长航已经不是“长航”了,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国际船舶公司。我有幸跑过东南亚一些国家,前年跑了中东,去年跑的是大洋洲,还真去了不少国家,长了不少见识呢。他说:真让人羡慕,没有赶上这样的好时光。跑中东,有海盗吧,要注意安全哟。我说:是有海盗,但有海军护航,有武装保安上船做保镖,船上还有防海盗设施,安全没问题。谢谢关心!他说:我经常看《长江航运报》,关注长航的发展,在上面搜寻一些老同事的消息,这不看到你的文章就耐不住给你打电话了吗……
放下电话,我的记忆一下回到了从前——八十年代,想到了他对我的照顾和关怀。1985年12月我才分配到南京长江油运公司拖轮长江62025上,不久他就调来了。因为是老乡,所以对我特别照顾,在我谈朋友出现纠纷时,他像兄长一样出面帮我调停,让我终身难忘。除此之外,他让我享有先看《长江航运报》的特权,让我觉得情深意长。那时候拖轮船上文化生活相对单调,船上就只有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工人日报》、《新华日报》和《长江航运报》等几份报纸,前两份谈的是国家大事,而新华日报谈的省市新闻,对于我没有多少吸引力,只有《长江航运报》,谈的企业“小事”,贴近我们的生活,我非常爱看,船上的年轻人与我一样也爱看《长江航运报》。所以,能优先看到《长江航运报》无形中被赋予特定的意义。为了使这种照顾不显得过于明显,每次,他都叫我去夹报纸,夹完之后,拿出去之前我就享用过“特权”了。
随着科技的发展,我以前干的报务员工作越来越受新技术的挑战,面临着岗位危机。这时候牟政委鼓励我多动笔,多读书,多看报,为将来转行奠定基础。看到报纸上文章,我真的很羡慕那些通讯员,他们的文笔那么好,写的那么自然。我从来就没有奢望自己的文章能登上报纸,因为我是一个理科生,高中时最差的就是语文,而语文最难的又是作文,我的作文在全班是垫底的,每次都在批评之列。但从那以后,我看报更用心了,开始学习《长江航运报》上文章了,有时牟政委也帮我分析一下他们的写作技巧。
2004年4月我开始做兼职政委,动笔多起来,也时不时向《长江航运报》投稿,2006年年底我转岗成为一名远洋船舶上的政委,《长江航运报》终于登了我写的文章,我不再是一名纯粹的看客。我都不敢想我真了成了我仰望已久的报纸——《长江航运报》的参与者,我很激动!
随着我的一些文章的登出,我也成了该报的受益者。2010年5月,我在浙江舟山碰到一个改行在南京外代做代理的同事王国平。我说:你还没有忘记我啊。他说:虽然5年未见面,但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你写的文章,想忘掉都不容易啊……前不久,我碰到一个驳船上转岗过来的水手长,当我自报家门后,他居然说认识我,见我一脸的茫然,他解释说:我在《长江航运报》上见过你写的文章。
是啊,我不也经常在报纸上寻觅故旧吗?休假的时候,我经常在网上看电子版的《长江航运报》,在上面见到熟人写的文章,觉得特别亲;看到以前同事成为报道中的主人翁,就打电话与他聊。对常见其名的如石连友等名人,则有想去拜访的冲动。
《长江航运报》自我分配到长航开始就一直伴随我成长,一晃三十年过去了,我已从一个小伙子成为半百之人,而它居然还长我十岁,经历了整整一个甲子。作为一个企业报,能在竞争激烈的报业毅立不倒实属不易,这与其办报特点有直接关系,它报道的重点在企业,写的是职工关心的事,与我们长航人的关系密切,企业和职工都需要它。老政委退休了都没有忘记它,说明它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
随着长航集团向海外扩张,集团所属的一些船舶航行于世界各地,这些船上的职工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方便地读到自己的报纸了。一个租期八个月,下船才能见它,上面的消息已成旧事,让人感觉它有点渐行渐远。什么时候能在远洋船上看到电子版的《长江航运报》就好了,能让这位老朋友——《长江航运报》陪伴我在浩浩大海上航行那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啊! (陈满林)